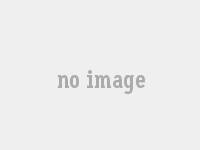“下葬遇五兆,后代出貴人”,古人眼中的五大天賜祥瑞
晚飯后,電視的聲音照例被開到35。新聞聯播的片頭曲像一把鈍鋸,不緊不慢地切割著客廳里凝固的空氣。我媽坐在沙發上,手里攥著遙控器,眼睛卻盯著那臺65寸的黑屏,屏幕上倒映著她空洞的臉。我爸去世的第三天,這個家就像一臺被拔掉電源的舊機器,所有齒輪都銹死在了最后一個瞬間。
那個瞬間,就是我爸坐在他專屬的藤椅里,指著電視,含混不清地對我說:“小默,聲音,35。”
我走過去,按下了遙-控器,屏幕右下角跳出綠色的數字“35”。我甚至沒有回頭看他一眼,只是不耐煩地“嗯”了一聲。那是我對他說的最后一句話。
現在,電視開著,音量35,但藤椅空了。
手機在口袋里震動,屏幕上跳動著兩個字:父親。我深吸一口氣,喉嚨里像堵了一團浸滿冰水的棉花。這是我爸的手機,現在在我媽手里。我劃開接聽,沒有說話。
電話那頭是我媽壓抑的、帶著鼻音的聲音:“小默,你大伯……他們來了。”
“嗯。”
“你爸……你爸他老家的意思,是想……落葉歸根。”
我捏著手機,指節發白。我爸是縣城工廠的退休工人,一輩子沒離開過我們這個三線小城。所謂老家,是那個我們只在清明節才會回去、連像樣公路都沒有的偏遠山村。
“媽,現在都什么年代了,公墓不都挺好的嗎?城里辦事也方便。”我的語氣很平靜,但我知道,這平靜是一層薄冰,下面是洶涌的煩躁和抗拒。
電話那頭是我媽長久的沉默。這種沉默比任何哭喊都更讓我心慌。我能想象到她在那頭,無聲地用手背抹著眼睛。
“你爸……他臨走前,一直念叨著老家后山的那棵黃桷樹。”
又是黃桷樹。我從小聽到大,那是我爺爺下葬的地方。我爸總說,那是個風水寶地。我小時候問他什么是風水寶地,他摸著我的頭,一臉向往:“就是能保佑我們家代代平安,保佑你以后出人頭地的地方。”
我考上大學,他覺得是黃桷樹顯靈。我進了大公司,他覺得是黃arlar樹保佑。我甚至覺得,我人生中所有的努力,在他眼里,都成了那棵樹的功勞。
“媽,那些都是迷信。”我終于還是沒忍住。
“小默!”我媽的聲音陡然尖銳起來,“這是你爸最后的念想!”
……
電話掛斷了。客廳里只剩下新聞聯播的聲音,字正腔圓,清晰得刺耳。我的目光掃過玄關的鞋柜,上面放著一個未開封的紅色禮盒,是我爸生日時,我托人買的兩瓶茅臺。他寶貝得不行,說要等我兒子考上大學再開。現在,這抹紅色像一道傷疤,烙在我的視野里。
口袋里的手機又震了一下,是一條短信。一個陌生的、來自老家區號的號碼,內容只有一句話:“陳默,你爸的事,有些東西你必須回來看看。”
我沒有回復。
我站起身,走到電視機前,拿起遙控器,想把聲音調小。手指懸在減音鍵上,卻怎么也按不下去。數字“35”,像一個烙印,燙得我指尖發麻。
最終,我關掉了電視。
巨大的寂靜瞬間將我吞沒。我猛地扭過頭,看向那把空蕩蕩的藤椅,仿佛我爸還坐在那里,用他那雙渾濁又固執的眼睛,靜靜地看著我。
引子
我叫陳默,名字是我爸取的。他說,希望我沉穩、默然,訥于言而敏于行。我做到了,至少表面上是。我在一家互聯網公司做項目總監,習慣了用數據、邏輯和KPI來構建我的世界。在我的世界里,一切都應該是可量化、可預測、可控制的。
除了我父親,陳建國。
他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變量。一個固執、傳統,將所有希望寄托于虛無縹緲的“運氣”和“風水”的男人。我們之間的溝通,像兩條永不相交的平行線。他談節氣養生,我談科學健身;他講鄰里人情,我講社會規則;他信奉“命里有時終須有”,我信奉“我命由我不由天”。
我們的每一次對話,幾乎都以我的沉默和他的嘆息告終。
他去世后的第四天,我還是開車回了老家。車子在嶄新的高速公路上飛馳,窗外是飛速倒退的城市剪影。我腦子里一片混亂,那個陌生號碼的短信,我媽口中的“最后念想”,還有那空蕩蕩的藤椅,交織成一張密不透風的網。
車下了高速,拐上顛簸的省道,再轉入塵土飛揚的鄉道。路越來越窄,兩旁的景象也越來越荒涼。最后,車停在了村口。大伯和幾個族親已經等在那里,每個人臉上都掛著一種程式化的悲戚。
“小默回來了。”大伯走上來,拍了拍我的肩膀,手掌粗糙得像砂紙。
我點了點頭,目光越過他們,投向村子深處。那是一個被時間遺忘的角落,泥土的墻,黑色的瓦,空氣中彌漫著牲畜糞便和潮濕草木混合的味道。這里的一切,都與我格格不入。
靈堂設在老宅的堂屋里。我爸的黑白照片掛在正中,他穿著一身嶄新的中山裝,嘴角微微上揚,眼神卻依然固執。我跪在蒲團上,燒了三炷香,煙霧繚繞中,照片里的他仿佛活了過來。
晚上,大伯把我叫到一邊,昏黃的燈泡下,他遞給我一支煙,自己點上一支,深吸一口,緩緩吐出。
“小默,你爸的后事,我們商量過了。就葬在后山,你爺爺旁邊。”
“大伯,現在都提倡火化,山上交通不便,以后祭拜也麻煩。”我盡量讓自己的語氣聽起來像是在商量,而不是頂撞。
大伯的眉頭擰成了一個疙瘩。“這是你爸的遺愿!他生前反復交代,一定要土葬,一定要在老地方。”他頓了頓,聲音壓得更低了,“而且,你爸專門請人算過,后天,是百年難遇的好日子。他說……他說只要下葬時能遇上五大祥瑞之兆,我們陳家后代,必出貴人。”
我心里的那股煩躁又升騰起來。“大伯,都什么年代了,還信這個?”
“你懂個毬!”大伯的情緒突然激動起來,一句粗俗的方言脫口而出,“你爸這一輩子,為了啥?不就為了你,為了你兒子!他自己沒本事,就想給你們掙個好兆頭!人活一口氣,樹活一張皮,你懂不懂!”
“什么是五大祥瑞?”我揉著發痛的太陽穴,下意識地重復著我那個標志性的小動作。我知道,每當我開始對一件事感到失控和荒謬時,我就會這樣。
大伯的臉色緩和下來,帶著一絲神秘和向往,一字一句地說道:“老祖宗傳下來的說法。‘下葬遇五兆,后代出貴人’。這五兆就是:第一,靈柩過家門,犬不吠;第二,起墳見活物;第三,入土逢甘霖;第四,下葬聞鳥鳴;第五,封土現金光。”
我幾乎要笑出聲來。這聽起來比我項目計劃書里的PPT神話還不靠譜。狗不叫?下雨?鳥唱歌?這也能算祥瑞?
“你別不信。”大伯看出了我的輕蔑,嚴肅地說,“你爸為了這事,準備了好幾年。他說,這是他能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
那一晚,我失眠了。躺在吱呀作響的木板床上,我爸那張固執的臉,大伯口中的“五大祥瑞”,還有那句“人活一口氣”,在我腦中反復回響。我感到一種巨大的荒謬感,仿佛被卷入了一場精心策劃的封建迷信戲劇。
而我,是那個唯一不愿配合的演員。
第一章 靈柩過門,犬不吠
出殯定在后天凌晨五點。
這兩天,老宅里人來人往,流水席從早擺到晚。我像個提線木偶,被大伯和族親們安排著做各種繁瑣的儀式。我媽一直陪在靈前,不怎么說話,只是默默地流淚,整個人像被抽走了主心骨。
我妻子林悅也帶著五歲的兒子小宇從城里趕了過來。她是個通情達理的女人,一到就挽起袖子在廚房幫忙,把小宇也看得很好。她私下里勸我:“陳默,爸都走了,就順著老人的意思吧。別讓你媽再難受了。”
我看著她,點了點頭,心里卻堵得更厲害了。她不懂,這不是順不順著意思的問題,這是兩種價值觀的根本沖突。我無法接受我父親的死,還要被這樣一場充滿愚昧色彩的儀式所綁架。
出殯前一晚,我接到了公司副總的電話,催我盡快回去,有一個重要的項目等著我拍板。我站在院子角落里,壓低聲音對著電話保證:“王總,我最遲后天晚上趕回去,資料我都看過了,方案沒問題。”
掛了電話,我一轉身,看到我爸的一個遠房堂弟,村里人叫他“陳三”,正蹲在不遠處的墻角,手里拿著一個蛇皮袋,鬼鬼祟祟地不知道在干什么。見我看來,他嘿嘿一笑,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含糊地說了句“幫忙,幫忙”,就溜走了。我沒在意,只當是村里人的怪癖。
凌晨四點,天還是一片漆黑,整個村子卻都醒了。老宅里燈火通明,哀樂聲低低地響著。按照規矩,長子長孫要捧著靈位,走在隊伍的最前面。我換上了一身孝服,麻繩勒得我皮膚生疼。
小宇被吵醒了,揉著眼睛,一臉茫然地問我:“爸爸,我們這是要去哪里?”
我喉嚨哽住,不知道該怎么回答。難道要告訴他,我們要去參加一場尋求“祥瑞”的盛大表演嗎?
林悅把他抱在懷里,柔聲說:“我們去送爺爺,送爺爺去一個很遠很美的地方。”
五點整,時辰一到,大伯高喊一聲:“起靈!”
八個壯漢抬起沉重的楠木棺材,緩緩走出堂屋。我捧著靈位,跟在后面,腳下像踩著棉花。送葬的隊伍很長,幾乎全村的人都跟在后面,默默地走著。
隊伍要繞著村子走一圈,這是規矩,叫“辭鄉”。
村子不大,但養狗的人家很多。平日里,別說這么大的動靜,就是一個陌生人進村,都能惹得群犬沸騰。我繃緊了神經,幾乎已經預感到接下來那片嘈雜的犬吠聲,將如何把這場莊嚴肅穆的送行,徹底撕成一個笑話。
然而,隊伍從村東頭走到村西頭,一路寂靜無聲。
沒有一聲狗叫。
那些平日里最是兇悍的土狗,此刻都像是被施了定身法,有的趴在窩里,有的臥在門前,只是抬起眼皮,默默地看著隊伍走過,喉嚨里連一絲嗚咽都沒有。
整個村子,除了送葬隊伍的腳步聲和低回的哀樂,再無雜音。
這寂靜,安靜得詭異。
我身后的村民開始竊竊私語。
“怪了,今天這些狗怎么都啞巴了?”
“是啊,老陳家的福氣啊!”
“這第一兆,‘靈柩過家門,犬不吠’,應驗了!”
我聽著這些議論,心里非但沒有感到絲毫敬畏,反而升起一股強烈的荒誕感和被算計的憤怒。這太不正常了。巧合?我不信。我猛然想起了昨晚那個鬼鬼祟祟的陳三。
隊伍在村口停下,準備上山。我找到大伯,把他拉到一邊,壓著火氣問:“大伯,這到底是怎么回事?村里的狗為什么不叫?”
大伯的臉在黎明的微光中顯得很模糊,他躲閃著我的目光,只是含糊地說:“你爸在天有靈,都有感應。”
“你別跟我說這些!”我的聲音不由得大了起來,“是不是你們做了什么手腳?”
大伯被我問得急了,終于低吼道:“是!是你爸提前安排的!他給了陳三兩千塊錢,讓他提前一晚,挨家挨戶去打了招呼,送了肉骨頭!讓各家在出殯的時候把狗拴好,嘴套上!這下你滿意了?”
我的腦子“嗡”的一聲。
原來如此。
所謂的“天賜祥瑞”,不過是一場處心積慮的人為表演。我爸,我那個固執而要強的父親,他不是在等待奇跡,他是在制造奇跡。
我看著那口沉重的棺材,心里五味雜陳。那里面躺著的,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父親?他用這樣笨拙甚至有些可笑的方式,試圖為我,為這個家,鋪就一條他想象中的“青云路”。
“小默……”大伯的聲音軟了下來,“你爸他……他不容易。他總覺得沒給你留下什么,這是他唯一能做的了。”
我沒有再說話,只是默默地轉過身,重新回到隊伍前面。捧著靈位的手,感覺重了千斤。那冰冷的木牌上,刻著“先考陳公建國之位”,此刻在我眼中,卻化成了我父親那張飽經風霜、寫滿期盼的臉。
天邊,開始泛起魚肚白。山路崎嶇,隊伍走得更慢了。
第二章 起墳見活物
后山不高,但路很陡。所謂的路,不過是人們踩出來的泥土小徑,被清晨的露水一打,濕滑難行。
我們走了將近一個小時,才到達半山腰那棵巨大的黃桷樹下。這里視野開闊,可以俯瞰整個村莊。我爺爺的墳就在樹下,已經長滿了青草。旁邊,一個新的墓穴已經挖好,旁邊堆著新鮮的黃土。
幾個負責挖墓的壯漢正蹲在一旁抽著旱煙,看到我們來了,紛紛站起身。其中一個領頭的,叫李老四,走過來對大伯說:“建軍哥,都弄好了,時辰差不多了。”
大伯點了點頭,指揮著眾人將棺材小心翼翼地抬到墓穴旁。
按照風水先生的說法,吉時在上午九點。還有一個多小時,大家便各自找地方歇腳。我媽在爺爺的墳前跪下,撫摸著墓碑,肩膀一聳一聳的,無聲地飲泣。林悅陪在她身邊,輕輕拍著她的背。小宇大概是累了,靠在林悅懷里睡著了。
我走到墓穴邊,往里看了一眼。坑挖得很深,四四方方,像一個通往未知的入口。我的目光落在新翻的泥土上,突然,我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
在堆積的泥土邊緣,有一小片地方的土質顏色不太一樣,顯得更濕潤、更疏松。而且,那里似乎被什么東西小心地覆蓋著,像是一個倒扣的竹篩。
我的心猛地一跳。聯想到第一個“祥瑞”是人為制造的,一個念頭不可遏制地冒了出來。
我走過去,裝作不經意地問正在收拾工具的李老四:“李師傅,這墳挖了多久?”
李老四憨厚地笑了笑:“昨天下午就開始挖了,挖了半天呢。你爸選的這地方,土好。”
“挖的時候,沒碰到什么石頭或者樹根之類的?”我繼續試探。
“沒有,順當得很。”李老四說著,眼神卻下意識地往那個蓋著竹篩的地方瞟了一眼。
這個細微的動作沒有逃過我的眼睛。我幾乎可以肯定,那里有問題。
我沒有聲張,只是默默地走開,坐到一棵樹下,冷眼旁觀。我倒要看看,我那個“深謀遠慮”的父親,和我這些“忠心耿耿”的族親,接下來要上演哪一出戲。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太陽越升越高,山里的霧氣漸漸散去。
九點整,風水先生看了一眼羅盤,高聲喊道:“吉時已到!準備落棺!”
大伯立刻打起精神,指揮眾人開始最后的準備。就在這時,異變突生。
一直蹲在墓穴旁幫忙的陳三,突然“哎喲”一聲大叫起來,指著那堆新土,聲音里充滿了夸張的驚恐和喜悅:“快看!快看!這是什么!”
所有人的目光瞬間被吸引過去。
只見陳三一腳“不小心”踢翻了那個我早就注意到的竹篩,從下面松軟的泥土里,猛地竄出一條黑色的東西!
那是一條蛇!
一條將近一米長、通體烏黑的蛇。它似乎被這突如其來的變故驚嚇到,昂著頭,吐著信子,警惕地看著周圍的人群。
人群瞬間炸開了鍋。
“蛇!是蛇啊!”
“黑蛇!這是‘烏龍’啊!是龍!”
“天哪!‘起墳見活物’!這第二兆也應了!老陳家這是要大發了!”
村民們的臉上寫滿了敬畏和羨慕。我媽也止住了哭聲,愣愣地看著那條蛇,眼神里流露出一絲希望的光芒。大伯更是激動得滿臉通紅,嘴里不停地念叨著:“顯靈了,顯靈了……”
我冷冷地看著這一切,看著那條在原地盤旋、卻并不急于逃走的蛇,看著陳三那浮夸的演技,看著眾人那被輕易煽動的狂熱。
我的心,一點點沉了下去。
如果說第一個“祥瑞”還只是讓我感到荒謬,那么這第二個,則讓我感到一陣深刻的悲哀。為了一個虛無縹緲的“貴人”夢,他們竟然可以做到這個地步。這條蛇,十有八九是他們早就抓來,藏在那里的。
我站起身,撥開人群,一步步走向那條蛇。
“小默,你干什么!別傷了它!這是靈物!”大伯急忙想拉住我。
我沒有理他,只是死死地盯著那條蛇。它也看著我,三角形的腦袋微微晃動。突然,我停下腳步。
我看到,在蛇的七寸位置,有一圈極不明顯的、淺淺的白色印記。那像是一個被繩子或鐵絲捆綁了很久之后留下的痕跡。
我的心,像是被針狠狠地扎了一下。
這條蛇,不是野生的。它被人抓來,捆綁,餓了幾天,然后在“恰當”的時機被放出來,配合他們演完這場戲。演完之后呢?它的命運又將如何?
我緩緩蹲下身,與那條黑蛇對視。在它冰冷的、不帶任何感情的瞳孔里,我仿佛看到了另一個自己。一個同樣被無形的繩索捆綁,被迫參與這場荒誕劇目的自己。
這一刻,我對父親的怨懟,對族親的鄙夷,突然都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深入骨髓的無力感。
我緩緩伸出手,不是去抓它,而是做了一個“請”的手勢。
那條蛇仿佛看懂了我的意思,它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身體一扭,像一道黑色的閃電,迅速鉆進了旁邊的草叢,消失不見了。
人群發出一陣惋惜的嘆息。
我站起身,回頭看著大伯和陳三,他們的臉上都有一絲不易察覺的慌亂。我沒有戳穿他們,只是平靜地說了一句:“吉時快過了,落棺吧。”
大伯愣了一下,隨即反應過來,連忙高聲指揮:“落棺!落棺!”
棺木緩緩沉入墓穴。我看著那口棺材,心里第一次有了一個疑問:爸,你到底背負著什么?為什么你寧愿用這種方式,也要給我一個“交代”?
第三章 入土逢甘霖
落棺之后,是填土。
親屬們輪流上前,抓起一把黃土,撒入墓穴。輪到我時,我抓起一把冰冷的泥土,泥土從指縫間滑落,沙沙地打在棺蓋上。那聲音,像是時光流逝的回響。
我突然想起小時候,有一次我發高燒,爸背著我,在雪地里走了十幾里山路,把我送到鎮上的衛生院。他的背很寬,很暖,趴在他的背上,我能聽到他沉重而有力的心跳。那時的他,是我心中無所不能的神。
是從什么時候開始,他變成了現在這個固執、迂腐,甚至有些可笑的老頭?
是我長大了,還是他變老了?
我站起身,默默退到一邊。林悅走到我身邊,把睡醒的小宇交給我,自己上前去填土。小宇在我懷里,好奇地看著眼前的一切,小聲問:“爸爸,爺爺是不是睡在那個大盒子里了?”
“嗯。”我抱著他,感覺他的身體溫熱而柔軟。
“他會冷嗎?”
“不會的。”
“那我們什么時候能再見到他?”
孩子無心的一句話,像一根針,精準地刺入我心中最柔軟的地方。我用力眨了眨眼,把涌上來的酸澀感壓下去,只是更緊地抱了抱他。
填土進行得很順利。風水先生掐算著時間,指揮著眾人。按照他的說法,必須在正午之前,將墳墓徹底封好。
天氣一直很好,陽光燦爛,天空像一塊湛藍的絲綢。我抬頭看了一眼太陽,心里冷笑。這第三兆“入土逢甘霖”,看來是沒希望了。我甚至有些期待,期待這場鬧劇能在這里畫上一個句號,讓所有人都清醒一點。
然而,就在墳土即將封頂的時候,天空卻毫無征兆地起了變化。
剛才還晴空萬里的天,西邊突然涌來一大片烏云,像打翻的墨汁,迅速在藍色的畫布上浸染開來。太陽被遮蔽,光線一下子暗淡下來,山風也驟然變大,吹得樹葉嘩嘩作響。
“要下雨了!”人群中有人喊道。
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活,抬頭望天。
大伯的臉上,露出了難以置信的狂喜。他抓住我的胳膊,用力搖晃著,聲音都變了調:“小默!你看見沒有!要下雨了!要下雨了!你爸他真的……真的……”
他激動得說不出話來,眼眶卻紅了。
我看著天,又看了看手機上的天氣預報。APP上顯示,今天一天都是晴天,降水概率為零。我早上還特意看過,想以此來反駁他們。但眼前這翻臉比翻書還快的天氣,卻像一個響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我的“科學”和“邏輯”上。
我教過我爸用智能手機,教過他怎么看天氣預報。有一次他說明天膝蓋疼,可能要下雨,我還不耐煩地打開APP給他看:“爸,你看,這上面說明天是大晴天,你那都是心理作用。”
結果第二天,真的下了一整天的雨。他沒說什么,只是在我面前,默默地揉著自己的膝蓋。
現在,這匪夷所思的一幕,再次上演。
“嘀嗒。”
一滴冰冷的雨水,砸在我的額頭上。
緊接著,第二滴,第三滴……
密集的雨點,毫無預兆地從天而降,瞬間織成了一張巨大的雨幕。沒有狂風,沒有雷電,就是這樣溫柔而綿密的甘霖,悄無聲息地灑向這片山林,灑向這座新墳。
雨水打濕了泥土,散發出一種清新的氣息。
送葬的人群非但沒有躲避,反而都站在雨中,任憑雨水沖刷。他們的臉上,不再是狂熱,而是一種近乎虔誠的敬畏。仿佛這不是一場普通的雨,而是來自上天的洗禮和恩賜。
“入土逢甘霖……真的……真的應驗了……”有人喃喃自語。
我站在雨中,任憑冰冷的雨水順著我的臉頰滑落。我沒有動,也沒有說話。我的大腦一片空白。
如果說前兩個“祥瑞”是人為,那么這場雨,又該如何解釋?難道我爸真的能通天,連老天爺都來配合他演這場戲?
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徹底打亂了我的認知。我一直引以為傲的理性,在這場無法解釋的雨面前,顯得那么蒼白無力。
我看到我媽,她沒有哭,只是仰著頭,讓雨水落在她滿是皺紋的臉上。她的嘴角,竟然帶著一絲微笑。那是一種卸下所有重擔后,發自內心的、安詳的微笑。
那一刻,我突然覺得,這場雨是真的還是假的,或許已經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它給了生者慰藉。
雨不大,下了十幾分鐘就停了。烏云散去,太陽重新露了出來。一道絢麗的彩虹,橫跨在東邊的山谷之上,如夢似幻。
所有人都被這雨后的奇景驚呆了。
風水先生激動地喊道:“雨過天晴見彩虹!大吉之兆!大吉之兆啊!”
人群再次沸騰。
而我,卻在所有人的歡呼聲中,看到了一個被忽略的細節。在不遠處的山坡上,幾個陌生的男人,正手忙腳亂地收拾著一些我看不清的設備,然后迅速消失在樹林深處。
我的心,又一次沉到了谷底。
人工降雨?
這個瘋狂的念頭,像一道閃電,劈開了我混亂的思緒。我猛地看向大伯,他的眼神躲閃,不敢與我對視。
我什么都明白了。
我感到一陣徹骨的寒意,比剛才的雨水還要冰冷。我那個可敬又可悲的父親,他到底為了這場“祥瑞”大戲,付出了多少?他從哪里來的錢,去請人制造這一場又一場的“奇跡”?
我們家,并不富裕。他和我媽的退休金加起來,一個月不過五千塊錢。為了給我買婚房,他們幾乎掏空了所有積蓄。
我不敢再想下去。
我走到新墳前,看著那濕潤的黃土,輕聲說了一句誰也聽不見的話:
“爸,你到底想做什么?”
第四章 一個父親的獨白
【第三人稱上帝視角】
陳建國知道自己時日無多了。
在醫院的最后一個月,他大部分時間都是昏睡的。偶爾清醒的時候,他也不說話,只是睜著眼睛,固執地看著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塊水漬,形狀有點像老家后山的那棵黃桷樹。
他想起了自己的父親,那個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老實人。臨終前,父親拉著他的手,說的最后一句話是:“建國,爹沒本事,沒讓你過上好日子。以后……咱家的根,就靠你了。”
這句話,像一根刺,扎了陳建國一輩子。
他覺得自己辜負了父親的期望。他進過工廠,當過工人,努力了一輩子,最終也只是個普通人。他沒能讓陳家光宗耀祖,也沒能給兒子陳默一個更高的起點。
陳默是他這輩子最大的驕傲,也是最大的心病。
兒子聰明,有出息,在大城市站穩了腳跟,比他強一百倍。但陳建國總覺得,兒子的脊梁,不夠硬。他太順了,也太傲了。他只信自己,不信命,不信祖宗。他覺得兒子心里,缺了一口氣。一口“我是陳家子孫,我背后有靠山”的底氣。
這口氣,陳建國給不了他。他給不了兒子金山銀山,也給不了他權勢人脈。他唯一能給的,是一份虛無縹緲,卻又重如泰山的“祖宗庇佑”。
所以,他開始策劃自己的葬禮。
從五年前開始,他就在為這件事做準備。他翻遍了老家的縣志和各種雜書,找到了那個“下葬遇五兆,后代出貴人”的說法。他覺得,這是他能為兒子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開始存錢。他戒了煙,戒了酒。他和老伴省吃儉用,把每一分退休金都掰成兩半花。他跟陳默說自己膝蓋疼,其實是偷偷跑去工地打零工,摔的。他跟老伴說去公園下棋,其實是去廢品站賣紙箱和瓶子。
五年,他偷偷攢下了八萬塊錢。這是他的棺材本,也是他為兒子導演這場“祥瑞”大戲的全部預算。
他找到了遠房堂弟陳三,一個在村里游手好閑,但腦子活絡的人。他給了陳三兩千塊,讓他負責“犬不吠”的環節。
他又找到了村里挖墓的李老四,多給了五百塊的“辛苦費”。他告訴李老四,挖墳的時候,如果看到蛇洞,千萬不要驚動,悄悄用東西蓋好就行。他知道那片山地,有一窩常年盤踞的烏梢蛇,無毒,但看著唬人。這是他為“起墳見活物”埋下的伏筆。
最難的,是“入土逢甘霖”。
他查了一年的天氣資料,又托城里的親戚,輾轉聯系上了一家專門搞人工增雨作業的公司。對方一開口,就要五萬。這幾乎是他全部的積蓄。
他猶豫了很久。那天晚上,他夢到了自己的父親。父親還是那句話:“建國,咱家的根,就靠你了。”
他醒來,一身冷汗。第二天,他把錢打了過去。他跟對方約好,只要他這邊一個電話,不管什么天氣,兩個小時內,必須讓后山那片地方下雨。
他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得妥妥當帖,像一個即將上戰場的將軍, meticulously 檢查著自己的每一個士兵和每一件武器。
他甚至想好了,如果這些都失敗了怎么辦。他準備了一個大號的藍牙音箱,里面下載了各種鳥叫的聲音,準備在“下葬”時播放。至于“現金光”,那只能看天意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他已經盡了自己全部的力氣。
做完這一切,他感覺身體被掏空了。但他心里,卻前所未有的踏實。
他覺得,自己終于可以去見父親了。他可以挺起胸膛,告訴他:“爹,我沒本事,但我給咱陳家的后人,請來了一場天大的祥瑞。咱家的根,以后會扎得更深,長得更高。”
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躺在病床上,看著窗外。他想的不是自己即將到來的死亡,而是兒子陳默。他想象著,當陳默親眼看到那五大祥瑞一一應驗時,會是怎樣震驚和敬畏的表情。
他希望,從那一刻起,陳默能夠相信,自己不是一個人在奮斗。他的背后,有祖宗,有神靈,有這片生他養他的土地。
他希望,這場他用盡生命最后一點力氣導演的大戲,能成為兒子心中一根永遠挺立的脊梁。
人活一口氣。他陳建國,要為兒子,爭下這口氣。
他慢慢地閉上眼睛,嘴角,帶著一絲心滿意足的微笑。
第五章 下葬聞鳥鳴
【第一人稱“我”視角】
一場精心策劃的雨,澆滅了我心中最后一點僥幸。
我站在那里,像一個局外人,冷冷地看著眼前這出荒誕的悲喜劇。村民們的歡呼,大伯的眼淚,我媽臉上重燃的希望……這一切都像一把把鈍刀,反復切割著我的神經。
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孤獨。在這個被“祥瑞”光環籠罩的山坡上,只有我一個人,是清醒的,也是痛苦的。
封土還在繼續。雨后的泥土變得泥濘,人們的動作卻更加賣力了。仿佛他們堆砌的不是一座墳,而是一座通往榮華富貴的金字塔。
我沒有再去看那些可能存在的“演員”,也沒有再去質問大伯。因為我知道,一切都無濟于C事。這是一場我父親用生命做賭注的局,所有人都深陷其中,心甘情愿。
我的目光,落在了那口已經被黃土覆蓋大半的棺材上。
爸,你究竟是傻,還是聰明?你用一場彌天大謊,換來了所有人的心安理得。可你有沒有想過,當謊言被揭穿的那一天,他們該如何自處?我又該如何自處?
“爸爸,你看,鳥!”
小宇清脆的聲音,打斷了我的思緒。
我順著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見幾只色彩斑斕的畫眉鳥,不知何時落在了不遠處的樹枝上,正歪著腦袋,好奇地打量著我們。
緊接著,一聲清脆悅耳的鳥鳴,劃破了山谷的寧靜。
“啾——啾啾——”
仿佛是一個信號,四面八方的樹林里,都響起了此起彼伏的鳥鳴聲。畫眉、喜鵲、百靈……各種我叫不出名字的鳥兒,像是赴一場盛大的音樂會,用它們最婉轉動聽的歌聲,為這場葬禮伴奏。
歌聲清越,悠揚,沒有絲毫悲戚,反而充滿了勃勃生機。
“第四兆!‘下葬聞鳥鳴’!”風水先生的聲音再次響起,帶著一絲顫抖,“四兆連珠!四兆連珠啊!這是何等的福報!”
人群已經從沸騰轉為肅穆。所有人都屏住呼吸,靜靜地聆聽著這場由百鳥合唱的安魂曲。他們臉上的表情,已經無法用簡單的“敬畏”來形容,那是一種親眼見證神跡的震撼。
我卻在這一片天籟之音中,感到一陣刺骨的寒意。
我下意識地尋找著聲音的來源。我的目光在周圍的樹林里逡巡,試圖找出那個隱藏的藍牙音箱。我敢肯定,這又是他們安排好的戲碼。
然而,我看遍了所有可疑的角落,都沒有發現任何人為的痕跡。那些鳥兒,真真切切地停在樹枝上,鼓動著它們的喉嚨,放聲歌唱。它們的神態那么自然,那么靈動,絕不是錄音所能模仿的。
難道這一次,是真的?
這個念頭剛一冒出來,就被我立刻掐滅。不可能。這個世界上沒有神跡,只有邏輯和概率。
我走到林悅身邊,她正抱著小宇,一臉驚奇地聽著鳥鳴。我壓低聲音問她:“你有沒有覺得,這鳥叫聲有點……太準時了?”
林悅愣了一下,隨即明白了我的意思。她皺了皺眉,輕聲說:“陳默,別想那么多了。或許……就當是爸在天有靈吧。”
連她也……
我感到一陣無力。我發現自己就像一個試圖在教堂里宣講無神論的瘋子,沒有人會相信我,他們只會覺得我不可理喻。
爭吵中,林悅下意識地從包里拿出我的保溫杯,擰開,遞到我嘴邊。這是一個我們之間持續了多年的習慣,每次我情緒激動,她都會這樣做。溫熱的水滑過我的喉嚨,讓我焦躁的心稍微平復了一些。
我看著她,她的眼神里充滿了擔憂。我突然意識到,我的固執和鉆牛角尖,或許也正在傷害她。
我沒有再說話,只是轉過頭,繼續看著那座即將成型的新墳。
大伯走到我身邊,拍了拍我的肩膀。他的手有些顫抖,不是因為冷,而是因為激動。他湊到我耳邊,用一種近乎耳語的聲音說:“小默,信了吧?你爸他……沒騙我們。”
我看著他通紅的眼眶,看著他那張被歲月刻滿溝壑的臉,那句“這也是你們安排的吧”到了嘴邊,卻怎么也說不出口。
我能說什么呢?
戳穿這一切,告訴他這是一場騙局?然后看著他和他身后那些淳樸的村民們,從希望的云端跌落到失望的谷底?看著我媽剛剛平復的心情,再次被撕裂?
值得嗎?
“人活一口氣。”
我爸的口頭禪,再次在我腦中響起。
這一刻,我好像有點明白他了。他爭的這口氣,或許不是給老天看的,也不是給祖宗看的。
是給活人看的。
是給我,給我媽,給所有關心這個家的人,一個繼續前行的希望和理由。
我緩緩地,點了點頭。
大伯看到我點頭,如釋重負地長出了一口氣,眼淚終于掉了下來。他用力地拍著我的背,嘴里反復說著:“好,好,這就好……”
百鳥的鳴叫聲漸漸停歇,仿佛是完成了它們的使命。
墳,也終于封好了。
第六章 封土現金光
墳墓封頂,立好墓碑。我爸的名字,和我爺爺的名字,并排刻在了一起。兩個平凡的男人,兩段沉默的人生,從此在這片黃土下,永遠相伴。
風水先生看了看天色,宣布儀式結束。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氣,仿佛完成了一件天大的事。大伯指揮著幾個年輕人,開始收拾東西,準備下山。村民們三三兩兩地聚在一起,興奮地討論著剛才發生的“四大祥瑞”,每個人都與有榮焉,好像陳家的福氣,也能分給他們一杯羹。
我站在新墳前,久久沒有動。
五個祥瑞,已經應驗了四個。雖然我知道,其中至少有三個是人為的,但那種被巨大力量裹挾的感覺,依然讓我心神不寧。
只剩下最后一個了——“封土現金光”。
我抬頭看了看天。雨后的天空,被洗得一塵不染。太陽高懸在頭頂,光線很足,但并沒有什么特別之處。
看來,這場大戲,終究是差了最后一幕。我心里,竟有了一絲說不清道不明的遺憾。
或許,連我自己都開始期待,期待一場真正的神跡,來為父親這荒誕卻又悲壯的執念,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
就在我們準備下山的時候,那個一直很安靜的陌生號碼,又一次打進了我的手機。
我走到一邊,按下了接聽鍵。
“喂,是陳默吧?”電話那頭,是一個略帶沙啞的男人聲音。
“是我,你是哪位?”
“我是你們村的村支書,我叫李建民。你……現在在后山上?”
“對。”
“那就好,那就好。”電話那頭的聲音聽起來有些焦急,“你聽我說,你爸……陳建國,他前幾個月找過我。他……他拜托我一件事。”
我的心猛地提了起來。
“他說,如果他走了,葬禮上,萬一……萬一那幾個兆頭沒湊齊,讓我無論如何,幫他圓上最后一個。”村支書的聲音頓了頓,似乎在組織語言,“他給了我五千塊錢,讓我在你們封土的時候,找幾個人,在對面的山頭上,用大鏡子,把太陽光反射到墳上,造一個‘金光’出來。”
我的手,猛地攥緊了。
“可是……”村支書的聲音充滿了歉意,“今天早上,我婆娘突然急性闌尾炎,我送她去縣醫院了,手機也落在家里了。我剛做完手術出來,才看到你大伯打了幾十個未接電話。我……我這事……我給辦砸了!我對不住你爸的囑托啊!”
電話那頭,是村支書懊惱的嘆息和自責。
而我這邊,卻是死一般的寂靜。
我掛了電話,感覺全身的力氣都被抽空了。我靠在一棵樹上,緩緩地滑坐到地上。
原來,最后一個“祥瑞”,也是假的。
犬吠、活物、甘霖、金光……全都是假的。全都是我那個可憐的父親,用他攢了一輩子的血汗錢,和我這些樸實的族親們,聯手為我上演的一出大戲。
只有那場百鳥朝鳳般的鳴叫,或許是唯一的變數,是這場精密騙局中,唯一的“天意”。
我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我只覺得心臟像是被一只無形的手緊緊攥住,疼得無法呼吸。
我那個傻父親啊!他以為自己安排得天衣無縫,卻不知道,他的每一個“錦囊”,都因為各種意外,以一種更加荒誕的方式,呈現在了我的面前。
他拼盡全力,想要給我一個神話。
而我,卻陰差陽錯地,窺見了這個神話背后,所有的心酸、笨拙和不堪。
“小默!快看!”
大伯的驚呼聲,將我從崩潰的邊緣拉了回來。
我抬起頭,順著所有人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見西邊的天空,剛才還晴朗無云,此刻卻又聚起了一片薄云。陽光透過云層的縫隙,投射下來,形成了一道道清晰可見的光柱,如同舞臺上的追光燈。
其中最亮、最粗的一道光柱,不偏不倚,正好籠罩在剛剛封好的那座新墳上。
黃色的墳土,青色的墓碑,在光柱的照耀下,仿佛鍍上了一層流動的金輝。光芒萬丈,神圣而莊嚴。
“金光……是金光!‘封土現金光’!”
“第五兆!五兆齊聚!我的天哪!”
“老陳家祖墳冒青煙了!不,是冒金光了!”
人群徹底陷入了瘋狂的膜拜。有人跪了下來,朝著新墳的方向不停地磕頭。我媽和我大伯,相擁而泣。
我看著這匪夷所思的一幕,看著這道精準得如同計算過的“神光”,腦子里只剩下村支書剛才的那句話:“我給辦砸了……”
他辦砸了。
可“金光”,還是來了。
這一次,不是人為。這一次,是真正的,無法解釋的天意。
我那個傻父親,他算計了一切,卻算漏了老天爺的心思。他用盡心機準備的“鏡子”,沒派上用場。而老天,卻用一場真正壯麗的“神跡”,補完了他劇本的最后一幕。
仿佛在對他說:孩子,你辛苦了。剩下的,交給我吧。
我再也控制不住,猛地扭過頭去,不想讓人看到我的表情。喉嚨里像是堵著一塊燒紅的炭,滾燙,刺痛。
我用力地眨著眼,想把那片模糊的景象看得更清楚一些。
在那片耀眼的金光中,我仿佛看到了我父親的影子。他穿著那身嶄新的中山裝,站在墳前,回頭看著我。他的臉上,不再是固執和期盼,而是一種如釋重負的、孩子般的笑容。
他沖我揮了揮手,然后轉身,走進那片金光,消失不見。
第七章 人活一口氣
下山的路,我走得渾渾噩噩。
耳邊是族親們興奮的議論,眼前是他們激動得通紅的臉。這場葬禮,在他們眼中,已經升華為一場家族傳奇。他們堅信,陳家的好日子,就要來了。
而我,是這個傳奇的核心,是那個被“天選”的后代。
沒有人注意到我的失魂落魄。他們都沉浸在“五兆齊聚”帶來的巨大喜悅中。
回到老宅,氣氛和來時已經截然不同。悲傷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壓抑不住的亢奮。大伯甚至破例拿出了我帶回來的那兩瓶茅臺,說要“告慰你爸在天之靈”。
我把自己關在房間里,躺在床上,睜著眼睛看著房梁。
犬吠是假的,活物是假的,甘霖是假的,金光……原本也準備是假的。
我父親,像一個最蹩腳的魔術師,用最拙劣的手法,準備了一場漏洞百出的表演。可偏偏,觀眾們都信了。甚至連老天,都忍不住下場,幫他圓了最后一個謊。
為什么?
我一遍遍地問自己。
晚上,我找到了獨自坐在院子里抽煙的大伯。
“大伯,你跟我說實話,我爸他……到底花了多少錢?”
大伯的身體僵了一下,手里的煙灰掉了一截。他沉默了很久,才啞著嗓子說:“你爸把他所有的積蓄,都花在這上面了。八萬塊。”
八萬塊。
這個數字,像一塊巨石,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
那是我爸和我媽省吃儉用一輩子,從牙縫里摳出來的錢。他本可以用這筆錢,去更好的醫院,用更好的藥,或許……或許能多活一段時間。
他卻用這筆錢,為我買了一場虛無縹緲的“祥瑞”。
“他就是個瘋子!”我終于忍不住,低吼了出來。
“他不是瘋子!”大伯猛地站起來,把煙頭狠狠地摔在地上,眼睛通紅地瞪著我,“他是你爸!他只是想讓你過得好!他覺得對不起你,沒能像別人家的爹一樣,給你鋪路搭橋。他怕你一個人在外面闖,被人欺負,被人看不起!他怕你心里沒底,走得不穩!”
“所以他就用這種騙人的方法?這就是他所謂的‘底氣’?”我幾乎是吼出來的。
“是!”大伯也吼了回來,“對你來說是騙局,對你爸來說,是他的命!他跟我說,小默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心太高,太傲,不信邪。他怕你這股傲氣,遲早有一天會把你壓垮。他要給你一個念想,一個寄托!讓你知道,你不是石頭縫里蹦出來的,你是有根的人!你背后,有祖宗保佑,有老天爺看著!你懂個毬!”
大-伯激動地揮舞著手臂,方言和粗話一起迸發出來。
我被他吼得愣住了。
“人活一口氣……”大伯的聲音低了下去,帶著一絲哽咽,“你爸常說這句話。他爭的這口氣,不是為了他自己,是為你爭的。他希望你以后,不管遇到多大的難處,多大的坎,一想到你爺爺下葬時這‘五大祥瑞’,你就能挺直腰桿,告訴自己,我是陳家的人,我是有福氣的人,我一定能扛過去!”
我呆呆地站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原來,這才是真相。
這不是一場封建迷信的鬧劇。
這是一個父親,用他最笨拙、最卑微,也最深沉的方式,為自己的兒子,舉行的一場盛大而悲壯的“加冕”儀式。
他不是要我出人頭地,當什么“貴人”。
他只是想在我心里,種下一顆名叫“信念”的種子。
他怕我走得太快,忘了回家的路。
他怕我飛得太高,忘了自己從哪里來。
我慢慢地蹲下身,雙手抱住頭,肩膀開始無法控制地顫抖。我沒有哭,只是感覺心臟的某個地方,徹底塌陷了下去。
那晚,我做了一個夢。夢里,我又回到了那個大雪天。我爸背著我,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在山路上。他的呼吸像一架破舊的風箱,呼哧呼哧地響。我趴在他背上,問他:“爸,我們還要走多久啊?”
他沒有回頭,只是用他那洪亮的聲音說:“快了,小默,翻過前面那個山頭,就到了。”
尾聲
我最終還是提前回了城。
臨走前,我把我錢包里所有的現金,都塞給了大伯。我說:“大伯,這些錢,你拿著。村里幫過忙的,一家家去謝謝。我爸欠的人情,我們不能不還。”
大伯看著我,點了點頭,眼眶又紅了。
我沒敢跟我媽告別。我怕看到她的臉,我會忍不住。
回到公司,我一頭扎進了那個被耽擱的項目里。我用瘋狂的工作來麻痹自己,試圖把那座山,那座墳,那片金光,都從我的腦海里驅逐出去。
但沒有用。
每到夜深人靜,我父親那張固執的臉,就會浮現在我眼前。
一個星期后,項目順利上線,慶功宴上,所有人都向我敬酒,說我力挽狂瀾,是公司最大的功臣。我端著酒杯,看著杯中搖晃的液體,眼前卻浮現出那兩瓶我爸沒來得及喝的茅臺。
我突然覺得索然無味。
我提前離席,一個人開車,在城市的立交橋上漫無目的地繞著圈。
車里的電臺,正放著一首老歌。
“……想得卻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該舍的舍不得,只顧著跟往事瞎扯……”
我的手機響了,是林悅打來的。
“老公,你回來了嗎?小宇在等你呢。”
“在路上了。”
“哦,對了,剛才你媽打電話來了。她說,她把你爸那個裝錢的鐵盒子打開了。”
我的心一緊。
“里面……沒有錢。”林悅的聲音有些遲疑,“只有一張紙條。上面是你爸的字。”
“寫的什么?”我把車停在路邊,手心全是汗。
林悅在那頭沉默了幾秒,然后一字一句地念道:
“給小默:
爸沒本事。這輩子沒給你留下金山銀山,只給你留下一場‘好運氣’。
信則有,不信則無。
爸只希望你,以后走累了,回頭看看。家,永遠是你的根。
人活一口氣。挺直了,走下去。”
電話這頭,我早已泣不成聲。
原來,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我會懷疑,知道我會調查,甚至知道我可能會戳穿這一切。
他留下的,不是一個完美的騙局,而是一個選擇題。
選擇相信,或者不信。
選擇活在冰冷的現實里,還是活在他用生命為我編織的、那個溫暖的謊言里。
我發動汽車,調轉車頭,向家的方向開去。
回到家,小宇已經睡了。他手里還攥著一個小木塊,是他在老家時,大伯給他削的。
我走進書房,從柜子最深處,拿出了那個紅色的茅臺禮盒。我打開它,給自己倒了一杯。
辛辣的液體滑過喉嚨,像一團火,從胸口一直燒到眼眶。
我看著窗外的萬家燈火,拿起了手機,撥通了那個熟悉的號碼。
電話響了很久才被接起,是我媽的聲音,帶著濃濃的鼻音。
“小默?”
我清了清嗓子,那聲“媽”在喉嚨里轉了千百回,最終,我用一種從未有過的、平靜而堅定的聲音,輕輕地說:
“爸。”
電話那頭,是我媽壓抑不住的、長長的抽泣聲。
而我,只是靜靜地聽著,看著窗外。
我知道,從今天起,我將帶著一場盛大的“祥瑞”,和我父親那句“人活一口氣”,走完我剩下的人生。
因為,我不再是一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