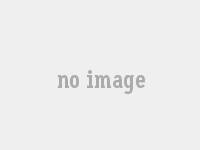臺灣杜月笙墓地:朝向上海,破敗寒酸,墓碑上方八個大字令人深思
在中國臺灣臺北大尖山下,空氣有點潮濕,草木藏著些許腐敗的味道。這里有一座老舊的墓地,顯然很久沒人來,誰都沒想到主人竟是鼎鼎大名的杜月笙!曾經混跡上海灘風頭無兩,如今卻只剩石碑上八個大字缺了閃耀的鋒芒。雜草瘋長,路全是荊棘。要不是有個素不相識的老人,每天自覺幫忙打掃整整三年,墳頭怕早淹沒在人們的遺忘里。偏偏,這八個字擺在那兒,“義節聿昭 譽聞永彰”,該夸贊的詞全給了。真配嗎?想想都有點別扭!

杜月笙,這個名字在歷史書上翻來覆去地出現過。有人說他是黑幫梟雄,有人說他是革命助手。光怪陸離的經歷讓人目眩。到底他跟那些名流大佬、老百姓、工人、革命黨人什么關系?幾句話也說不清。杜月笙成名之前只是個賣水果的,談不上什么魄力。他懶、愛賭博、天天瞎混。誰想到他后面會在上海灘翻云覆雨?沒誰能提前看穿。他站在他未來的路口時,和大多數普通人一樣糊里糊涂。
不過,人生的一腳踢出去,有時候就再也收不回來了。杜月笙混跡煙館,出門三分笑臉人,見多了上海灘的深淺。偶然結識青幫大佬陳世昌,才讓他爬上第一格梯級。這個城里頭的門道,杜月笙總能快人一步弄明白。他陰狠、狠辣、會做人,朋友都管他叫“杜先生”。倒時倒運,運氣卻總歸不賴。很快,他鉆進黑道,跟黃金榮、張嘯林結伙,開始做鴉片、走私,錢賺到出奇,名聲半黑半白,連上海警察都得裝聾作啞。

錢有了,手下也有,親信都是老油條,杜月笙最怕落個無名。后來想做點“正事”,權力才是最誘人的。他對蔣介石既有仰慕、也有戒備。時間來到1927年,北伐成功,國共表面合作。蔣介石正愁沒人打頭陣,杜月笙心思靈活,這會兒往政治場里擠。蔣介石看上他能打能殺,杜月笙則想借蔣的勢把名望穩穩立住。
但北伐后很快變天。四一二清黨,蔣介石翻臉如翻書,誰擋路誰遭殃。杜月笙接到活兒,跟黃金榮、張嘯林成立“中華共進會”,一夜之間,刀光劍影,血流成河。最慘的是汪壽華,工人運動領袖,被杜月笙設局請過去再活埋。杜月笙那會兒替蔣介石血洗街頭,轉頭等新局面。到底是投名狀還是一時意氣?還真說不清。

杜月笙這個人,總講義氣,但也總算計。他跟蔣介石的關系沒多少真正情分,更像是互相利用。蔣看杜月笙幫忙收拾“對頭”,可心想哪天這些老流氓對自己不利?先用再棄。杜月笙哪能不知道這點,他一邊拉攏蔣的信任,一邊捏著自己的底線。日本人勸杜月笙投降,開出了實在的條件,他也沒動心。但真有那么清高嗎?或許是心里明白:沒了上海,自己這條命也就不值錢了。
杜月笙總在上海混,他覺得人生不能太臟,但他沾的血遠不止一星半點。抗戰勝利那會兒,杜月笙回到上海,也有想再立個高臺坐坐。可他到家,上海市長、副市長已經定下,原定的大場面歡迎直接泡湯。滿街滿巷都貼著打倒“糞幫頭子”的標語,臉上不掛也難。所謂義氣、昔日情誼,統統從此斷了。杜月笙那句“夜壺理論”傳開了——不是自嘲,哪兒是夜壺、哪兒是馬桶,鬼才分得清。

有人說杜月笙不是沒試過去聯系共產黨,他幾次找過潘漢年,談了不少,嘴里是求寬大處理,話里含糊又多疑。他說話時心里打小算盤,生怕自己喊錯了隊伍被拉出去見閻王。解放前后,蔣介石一次次招呼他跟去中國臺灣。杜月笙既猶豫又害怕,留上海風險大,去中國臺灣心也不甘。他最后留在了香港,只想低調捱幾天。
但天不遂人愿。1949年,杜月笙昔日手下參與殺汪壽華的人落網槍斃,報紙上寫得清清楚楚。杜月笙看到,魂差不多嚇沒了,覺都睡不好,心跳老是停不了。人人都在說:紙包不住火,遲早輪到他。長年焦慮,杜月笙病得很重,整天躺著。有天,他忽然醒了,叮囑家人得穿長袍馬褂,好棺材送回上海,不管如何,寧可做個落魄鬼,總想著以后還得落葉歸根。這里頭的執念,不值錢但又特別的可惜。

1951年8月,杜月笙走了,死在香港出租屋。消息很快傳到蔣介石那邊,蔣表現得挺重情重義,請愿意讓杜月笙家人把他葬到中國臺灣。真是這么尊重他?其實未必,蔣介石那個時候,地盤丟光,人心散,正需要靠人情世故穩一點陣腳。杜月笙尸骨未寒,就被運去中國臺灣,住在臺北大尖山腳,風水上的說法還面朝上海。怎么安排的,這種操作總帶點舞臺劇的意味。
其實這里頭很多細節,冷暖早就無人說。杜月笙的第四房太太姚玉蘭艱難把遺體帶到中國臺灣,來回折騰,只有點親信幫忙。墓碑上的八個字,頭兩句是蔣親筆寫的,后兩句是張群撰的,意在表明此人名節昭著、德行天下。說得天花亂墜。可杜月笙這人,生前干過多少見不得光的事?舊賬一算,別說青史留名,連墓前干凈點都有點難為他。

很多年過去,那座墓地殘破到沒人愿意多看一眼,草深沒膝頭。陌生臺灣老人見不過去,出來義務清掃三年。有人覺得杜月笙也曾經是民族資本家,至少抗戰時沒給日本人低頭。還有些人則說,一輩子禍害百姓,殺人無數,有什么值得同情?不同人,不同說法。更尷尬的是,歷史上杜月笙曾多次向共產黨釋放出誠意,遞過橄欖枝,是出于自保還是投機?一時糊涂也罷,心懷鬼胎也罷,查不清全貌。
讓人感慨的是,早年一路靠刀尖上舔血爬上去,后來卻被老朋友遮遮掩掩嫌棄,靠家里女人安排后事。蔣介石明里暗里想用“反攻大陸”牌拉人氣,杜月笙自己其實也看得明白。不管怎么說,那個“義節聿昭,譽聞永彰”的墓碑,上下都帶著點嘲諷的味道。誰給誰留面,誰又能心安理得?亂世過去,立場和結局都變得模糊。
也許杜月笙一輩子的拼殺,到頭來沒有真正贏過一場。歷史的光怪陸離,不是誰干了什么就絕對壞,也不是誰站過哪里就全然是對。就像那句老話,現在說都覺得無力。畢竟人沒了,墓碑發黃,八個字再工整,里面的故事一個字都寫不全。
事實擺在那兒,杜月笙墳頭一草一木,都跟那八個字一樣尷尬。風吹雨打,反倒讓人看清了人間冷暖,一切虛頭巴腦,放下也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