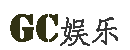《太虛幻境對聯》翻譯|原文|賞析|評點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太虛”即“太空”,“幻境”是虛幻而不存在的“環境”。在太空中一個虛幻并不存在的處所出現這副對聯,本身就有幾分玄虛。
這副對聯在書中共出現兩次。一次是在“甄士隱夢幻識通靈”之際,一次是在賈寶玉神游太虛境的時候,甄(真)賈(假)二人所見相同,這不是無意重復,而是有意向讀者暗示:甄士隱的遭遇和歸宿就是本書主人公賈寶玉人生歷程的縮影。
對聯的大意說:假的當作真的,真的也是假的;把無作為有,有也變成了無。如果太虛幻境是假的、虛無的,現實生活中的人間是真的、實有的,那么,這副對聯就是說:倘若把太虛幻境當作人間的話,人間就是假的;把太虛幻境當作實有的話,人間就是虛無的。不難看出,這其中包含著樸素的辯證觀點,作者用高度概括的哲理詩的語言,提醒讀者閱讀這部書時要辨清真的、假的和有的、無的,以免被假象迷惑,失去真意。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在閱讀時為了辨別真假有無而走入歧途,犯主觀臆斷、穿鑿附會的錯誤。魯迅先生在《集外集拾遺補編· 〈絳洞花主〉小引》一文中說:“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讀書望文生義、各取所需,就難免以假作真、無中生有。這樣看,對聯又有勸告讀者注意防止、盡量避免上述傾向的意圖。
那么,究竟應該怎樣進一步體會對聯所說的“真”和“假”呢?就全書來說,首先出場的“甄士隱”的名字便是“真事隱”的諧音。他與那位胡州(胡謅)人士賈雨村用“胡謅”的“假語村言”引出通篇故事,有意將一些有政治背景的“真事隱去”。絕不可認為作者有意玩弄文字游戲,在文字獄頗盛的清初,曹雪芹自有他的苦衷。作為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巨著,作者為了揭露封建地主階級潰滅的必然性,就只能將某些真實的東西隱藏在虛幻的外衣之下,讀者辨明這“真真假假”的含義,方能明確作者故意隱去的“真事”,體會到作品思想的真諦。基于上述原因,小說中“以假作真”的地方隨處可見。小說一開篇,甄士隱朦朧昏睡之際,夢見一僧一道暢談“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的“絳珠草”與“神瑛侍者”的感情糾葛。“瑛”即玉石,那么這里談的便是“一塊成了神的石頭”和一株“絳紅色的仙草”的故事。讀完全書,讀者不難明白這里說的是賈寶玉和林黛玉,這是以“假”作“真”;小說中寫曾經“接駕四次”的江南甄家,也和賈府一樣,有一個容貌相似、性情相同的甄寶玉,甄家和賈府一樣,后來也被抄了家。這是作者有意以“甄”亂“賈”,以“假”作“真”。再就“神游太虛境”這段情節本身的描寫來說,也是“假作真”的妙筆。寶玉上了秦可卿的臥榻,先說秦氏吩咐小丫環們去看“貓兒狗兒打架”,接下去便寫“那寶玉剛合上眼,便惚惚的睡去,猶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蕩蕩,隨了秦氏,至一所在”,后來警幻“授以云雨之事”,寶玉終至“柔情繾綣,軟語溫存,與可卿難解難分”,明眼人不難看出,這是真事假寫,或謂以假作真。作者不明寫秦可卿對寶玉的蠱惑勾引,卻以夢境委婉表達。仿佛似“無”,實際上卻“有”,這也就是“無為有處有還無”的真正含義。
從認識文藝作品反映現實這一點出發,正確理解《紅樓夢》這部巨著展示出的封建家族制度以及這種制度賴以生存的封建社會日趨敗落的景象,弄清對聯中所說的“真”與“假”、“有”和“無”是十分必要的。關于這個問題,魯迅在《三閑集·怎么寫》一文中曾有過精湛的論述:
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別人以敘自己,或以自己推測別人的東西,便不至于感到幻滅,即使有時不合事實,然而還是事實。其真實,正與用第三人稱時或誤用第一人稱時毫無不同。倘有讀者只執滯于體裁,只求沒有破綻,那就以看新聞記事為宜,對于文藝,活該幻滅。而其幻滅也不足惜,因為這不是真的幻滅,正如查不出大觀園的遺跡,而不滿于《紅樓夢》者相同。……我寧看《紅樓夢》,卻不愿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記》,它一頁能夠使我不舒服小半天。……幻滅以來,多不在假中見真,而在真中見假。
《紅樓夢》問世二百多年來,對于它的思想內容、社會意義曾有過種種歪曲,就是曹雪芹本人,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對小說中反映的某些社會現象,也不能從本質上去認識,所以當他提醒讀者識別真假、體會作品的思想精髓的時候,卻又不知不覺地流露了那么一點虛無主義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