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諸城八鄉(xiāng)里社,修家譜、查祖籍、探地名必備,關(guān)注收藏備用。
諸城,名字說起來簡單,背后可真不淺。早些年夏商時期,有個“諸”國在這片地頭晃悠,到了春秋魯國來了,秦漢又是瑯邪郡、東武縣一陣折騰。名字的變更和歸屬的變化說起來曲折,不是三言兩語能交代清楚的,說是地理沿革,倒還有點(diǎn)像老街巷里頭的家長里短,誰搬遷哪一戶,誰又改門換姓。這歷史,反正細(xì)節(jié)多得數(shù)不過來,蹉跎到隋代,才總算落了“諸城”這倆字。為啥叫諸城?歸結(jié)起來一句話,借山得名,東武山嘛。細(xì)問下去,城墻根下的老輩子們誰也說不全,也不想糾結(jié)這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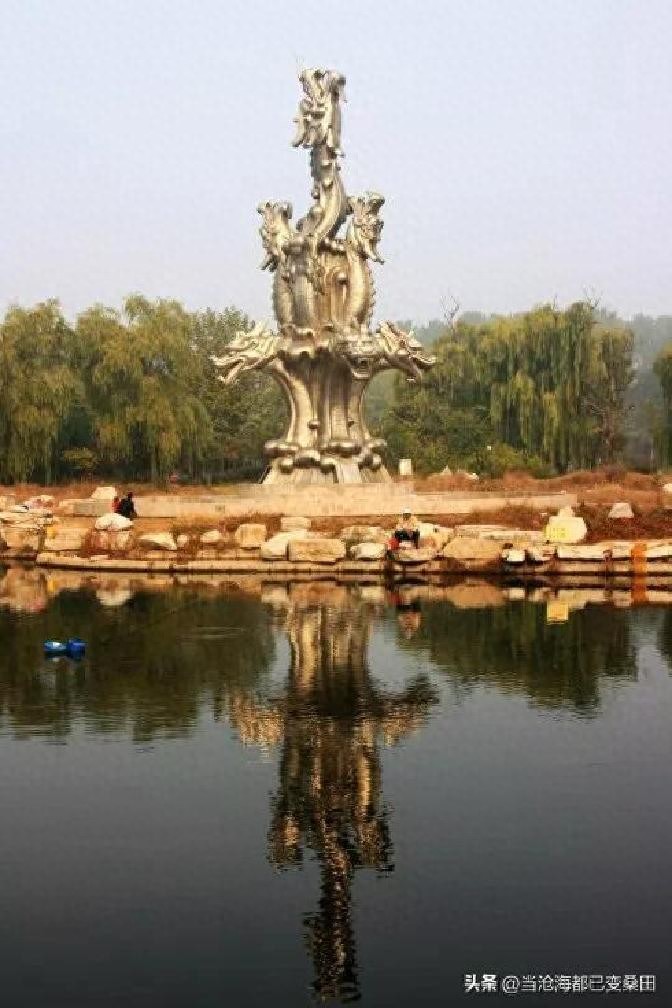
其實提起“里社”,跟現(xiàn)在講社區(qū)有點(diǎn)像,別以為那么復(fù)雜。明代開始,就講究一鄉(xiāng)分好幾社,社下分村。成天嚷嚷里社制度,其實就是數(shù)人頭、分農(nóng)田、派差役,都方便。那時候,一百多戶為一里,十戶出來推個頭,年年服差役,沒人愿意,那也得輪著。就像現(xiàn)在社區(qū)選個業(yè)委會主任,誰也不愿背鍋,還不是得走程序?明萬歷年間,八鄉(xiāng)里社框架搭得結(jié)結(jié)實實。甚至街坊傳說,還能對著舊志起哄,八成都忘了那些里長、社名,倒是哪個村誰家茄子長得好、誰家墻頭狗愛咬人,嚼得熱鬧。
翻明清的老志書,提這些社名、村名多得驚人,報恩鄉(xiāng)的全人社、福勝社、崇興社……順河社、朱村社、山前社,細(xì)列出來是密密麻麻。文獻(xiàn)里能找到村名的,多少還留了點(diǎn)傳承的線索。比如順河、潘旺、大王門、瓦店、焦家莊子、柴溝,各自在年代塵埃里扎了根。現(xiàn)在問,誰曉得報恩社里具體哪家劉姓發(fā)的財,十有八九沒法對上號,只能靠地皮上的傳說混個耳熟。

諸城的鄉(xiāng)社制度,倒真不覺得比大城市的小區(qū)樓盤遜色。古人分鄉(xiāng)八座,八鄉(xiāng)底下三五十社,再下面又分小村,據(jù)明代的記法,名字純靠地勢走向或是靠個地名隨便一取。有的社名是山水作證,有的則干脆因為有偏姓家族聚居,像是報恩社里東城后、西城后這種,隱隱帶著一種地緣的頑固。那老街坊鄰里之間,人情比地界還要分明。細(xì)覽下來,有些村名已變,有些則虛無縹緲,成了族譜上泛黃的幾頁,其實誰都解釋不清“消耗”是咋個意思,它不像水往低處流,一時盈一時縮。
有意思的是,細(xì)想那些村社的來歷,鄉(xiāng)下人城里人都喜歡編一堆軼事。比如大王門,諸城的王氏族源地,明清兩代都來回在志書里出現(xiàn)。傳到了新世紀(jì),光一個社區(qū),就有一堆名字。到了現(xiàn)代網(wǎng)絡(luò)時代,地名變社區(qū)名,歸屬也跟著行政調(diào)整搖擺,那能怎么辦?興許誰家祖墳頭還留著碑,才曉得大王門是王氏發(fā)家的地標(biāo)。而村社的劃分,外來人聽起來拗口;本地老人提起,卻都有故事傳。

瓦店,說起就能扯半天。往南,鄰著高疃,往東是潘家莊。管氏一族從海州搬來,說低洼就起個“凹甸”名,這好笑吧,結(jié)果諧音成了瓦店,甭說,挺貼切。過去那年月,趕集做買賣的多,也因交通便利,瓦店這小地頭,倒是比旁邊幾個村子來得熱鬧。古往今來,農(nóng)歷逢三八都趕場子。全羊老湯鍋,不試不知道,到了現(xiàn)場才曉得,諸城這類小集市能講出多少奇聞。
其實這么說,諸城地區(qū)的社戲、社集習(xí)俗才是鄉(xiāng)土生活的靈魂。魯迅寫“社戲”,其實道理一樣,農(nóng)村湊份子過春社,大村出戲班,小村合資捧場。趙莊、平橋,再大點(diǎn)的地方有演出,小村村民得出錢出人,難,誰也離不開誰。現(xiàn)在演變成廣場舞、小區(qū)合唱,形式變了,本質(zhì)沒變。你問原來社戲為啥這么熱鬧?再有知識的人說得清?也許這就是一種儀式感,春天來了,總得有點(diǎn)熱鬧。

某種意義上,八鄉(xiāng)里的分合、村社的興衰,很像社會的呼吸一樣起伏。風(fēng)水輪流轉(zhuǎn),今天有村明日沒人,舊志的“戶口消耗”,其實就是移民、衰敗,再繁華的社也可能變成荒草叢生的黃土垛子。柴溝,是個例外。高密、諸城兩縣分界,古時就治安混亂,甚至顧炎武都寫到這里盜賊多,設(shè)區(qū)長把守。明清時叫柴溝社,下面又有柴溝集、丘家大村,現(xiàn)如今還能找到些許當(dāng)年的遺跡,不過大多村落也都改頭換面,什么小溪橋梁、五龍河風(fēng)景……這些記載你要真讓歷史學(xué)家一一考證,八成會跑偏。
焦家莊子更有意思,名字里那個“子”字,明清志書、民國行政區(qū)劃、人民公社變化,一直到龍都街道,如今還沒變。明明早年屬于呂標(biāo)鄉(xiāng),行政區(qū)劃調(diào)整幾年一折騰,村社歸屬幾度變遷。可村民身份認(rèn)同反倒不怎么褪色。村落認(rèn)同,難道不是比所謂行政歸屬更牢靠些?

只是具體到細(xì)節(jié),有的村名從來沒正兒八經(jīng)對過號。比如有些社里頭一個村出現(xiàn)兩個劉家莊,明代分家、清代并村,后頭就理不清了,你要是執(zhí)著搞清楚今昔對比,反倒容易陷迷宮。歷史考據(jù),有時候就是這么吊詭。你硬說盛衰是天意,轉(zhuǎn)年又覺得是人力,這兩說法誰都說得過去。總有村落因遺忘冷落成段落邊角,偶爾亮相,也只是族譜某頁里發(fā)黃行文的一抹殘影。
數(shù)據(jù)呢?現(xiàn)在的互聯(lián)網(wǎng)資料也有用。2019年,諸城徐家洼整體搬遷楓香湖畔怡錦園,正兒八經(jīng)記得的也就剩下明丘橓墓在五里岡上。你說這變化算是進(jìn)步嗎?城市化浪潮里,老村被拆遷,族譜上記了一百年、兩百年的村名字一夜之間沒影了,有些人是會感慨的。可本地人說不定根本不當(dāng)回事,還覺得新小區(qū)大高樓才叫“興盛”。不是誰都醉心于歷史,更多人還是考慮自己能不能在新地界混口飯吃吧?

人口的盈縮,社會的更迭,權(quán)威史料記多少,終究落在村民柴米油鹽的小日子上。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口氣。明清官修,永遠(yuǎn)是新官上任忙著清戶清役,怕漏了哪個逃丁漏社;現(xiàn)在的網(wǎng)民可能更關(guān)心自家樓下小區(qū)的“業(yè)主群刷屏”、“誰家小區(qū)門口的快遞柜壞了”。時代變了,但那種“天地之間,村社更替”的底色,在這里就是這么過來的。
要說當(dāng)?shù)爻恋硐聛淼?“門道” 那還真是多,每一個名字后頭都有章有典,地名變遷、村落興衰,甚至是明清老志的注腳、現(xiàn)代網(wǎng)絡(luò)影像的補(bǔ)充,拼拼湊湊都不全。你要按數(shù)字分析,不靠譜;多角度看,似乎哪種說法都能成立。地理、歷史、心理、傳承,全堆在一起,齊魯大地的生土氣息還真不和別的地方一樣。

長這么大,哪座村社沒點(diǎn)混雜?不是每個社都能一眼望到頭。只有真正走到跟前,坐在老槐樹底下聽兩句嘮叨,看看新樓舊屋的交錯,或者在集市小攤上吸口羊湯鍋的氣味,才會明白諸城的八鄉(xiāng)里社,不就是我們這世世代代在這片地頭折騰出的生活印記嗎?
這些村村社社,各有各的運(yùn)氣和前因后果,一紙老志未必寫得清,人心里多少都有數(shù)。不是非要較個真。歷史像個不太服帖的老頑童,一會兒跳脫,一會兒又拘謹(jǐn),反正,諸城的故事,就在那里,不怕人問,也不怕人忘。




